杭州道教考古丨明代全真道士如何修行
欄目分類:玄門講經 發布日期:2017-06-16 瀏覽次數:次
文/劉康樂
杭州全真紫陽一派的代表者有徐弘道和丁野鶴等,南宗修道先命后性,然徐弘道有“不離本性即神仙”的悟道之語,似乎可以看出其對全真北宗的領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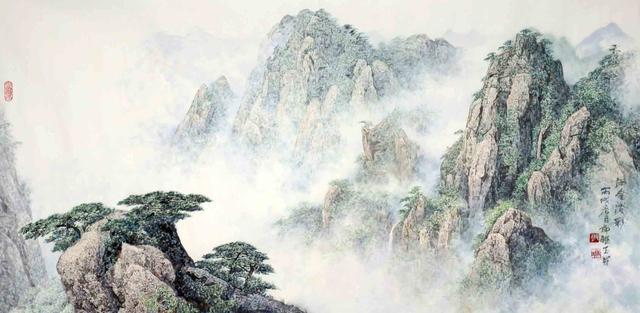
不離本性即神仙(資料圖 圖源網絡)
“師南而徒北”現象為何會出現
徐弘道高弟丁野鶴修道民間,“嘗沿門誦經,受少許米”,有化鶴之法,后全身坐化。對丁野鶴的師承和修證方法,《史方伯重修紫陽庵記》提出了疑問,“野鶴所證,蓋得北真之道者,而紫陽則張平叔別號也,又南真也。南真修形神俱妙,北真兼契虛無,其歸雖同,入則稍別。豈有師南而徒北耶?然不可考也。”實際上在元明之際,江南全真道士“師南而徒北”的現象,正是全真南北合流的現實反映,紫陽一派的修證方法也必受北宗的影響。
全真北宗著名道士閻希言
王重陽一派自稱“全真正宗”,為元代道教金丹派的主流,元滅南宋后,北方全真教大行于南方各地,杭州興建的全真宮觀中,有重陽庵、玉陽庵、長春庵、長生庵等,具有非常顯著的全真北宗色彩。然而可惜的是,明初杭州全真北宗并無高道而稍顯沉默,明中后期,有茅山乾元觀開山祖師閻希言,為江南地區全真北宗的著名道士,曾駐杭州雷峰塔,堅持苦行修道。

全真北宗著名道士閻希言(資料圖 圖源網絡)
據《萬歷錢塘縣志》載:“閻蓬頭希言,居雷峰最久,冬浴冰水,暑坐溺缶,出而暴之,無穢氣,勸人行陰騭,與巨公游,為筑巨麗宮觀,一日坐逝吳百戶家,百日猶生,請作偈曰:‘窮理盡性以至于命,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已’。”又有全真道士卓晚春,曾住杭州凈慈寺,《名山藏》載:“晚春,莆田人,生嘉靖間,自號無仙子,亦曰上陽子,人呼為小仙人……或走浴溪涘,飲水十數甌曰:‘漂我紫金丹也。’后脫化與杭州凈慈寺。”
全真教不同派別影響力
金蓬頭一派為元代全真南北二宗合流的結果。金蓬頭名志揚,號野庵,浙江永嘉籍全真道士,其師李月溪兼嗣全真南北二宗。元末金志陽與其同學桂心淵曾活動于福建武夷山、江西龍虎山一帶,元至元間卒,徒裔著名者有李全正、趙真純、馮蒲衣、楊古巖,再傳弟子趙宜真等。
趙宜真住江西紫陽觀,“于正乙、天心雷奧、全真還丹之旨,㫖多所發揮”,其弟子劉淵然創立“長春派”,為明代道教第一大宗派;而楊古巖在蘇杭一帶的影響深遠,此派道士以“明心見性、坐圜煉丹”為修行之本,但往往兼修正一諸派的道法,其徒倪玄素“于是守全真教、學正一宗,往來武當山中,遇至人教以禹步、飛岡之法、五雷金晶之書,修持不怠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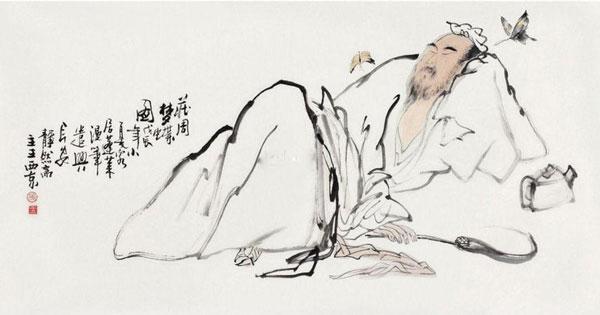
明心見性(資料圖 圖源網絡)
明初還有一派全真道士如張三豐、尹蓬頭、周顛仙等,與全真南北二宗皆無師承關系,可能來自于華山陳摶一派。鐘呂金丹派除張紫陽、王重陽分別創立全真南北二宗,還有精于周易和蟄伏的陳摶一派,此派道士善苦行,不修邊幅、言語瘋癲、行蹤神秘、起居無常,故多有“蓬頭”、“邋遢”、“顛仙”、“赤腳仙”之號,有神異和駐顏長壽之術,終以尸解仙去。
三豐道派發展狀況
明初張三豐與尹蓬頭、周顛仙、冷謙結伴云游金陵等地,據《朝天宮重建全真堂記》,“考之國初,圣祖楹圖一時,周顛仙、冷協律、張三豐、尹蓬頭皆以霞綃云佩之姿,從駕臨陣,浮波立浪。”三豐道派在杭州頗有傳人,如三茅觀張守常等,據《嘉靖仁和縣志》載:“(張三豐)嘗為天師郵書,張守常常疑墨濕,辟后山尋跡至寶極觀見焉,居歲余,聞胡濙至,竟遁去。”
張守常在明正統中曾為杭州府道紀司副都紀,同期重陽庵住持“(梅志)暹初受業三茅寧壽觀副都紀張靜庵為弟子”,則張守常很可能就是張靜庵,則明中后期的重陽庵全真道士中,頗有張三豐一派的傳人,如張復陽、梅志暹等。

張三豐(資料圖 圖源網絡)
明正統中重陽庵住持的全真道士梅志暹(又名道暹、古春),一方面繼承本庵自楊古嚴以至鐘本清(又名道銘)以來的金蓬頭道脈,另一方面“受業三茅寧壽觀副都紀張靜庵為弟子”,“又嘗受五雷之秘于富春周世昌。”這種復雜的學術背景,不僅在其全真身份中融匯了金志揚和張三豐的道脈,而且其所修持之法,除了全真丹法之外,還有“五雷秘法”等正一道法,“北宗、南宗及正一教多通而為一矣。”
“守全真教,學正一宗”
在明代重正一而抑全真的現實中,“守全真教,學正一宗”成為江南全真道士普遍實踐的修行之道。江南正一教盛行而民人崇奉法術,明后期杭州全真式微,吳山重陽庵似乎已為正一道士所掌,或者全真道士漸漸正一化,據《吳山重陽庵天醫行宮記》,“吳山重陽庵法師俞賓梅募建祠宇只奉陶吳許三真君……萬歷三年(1575)前住持陳日可、徒朱之一、徒孫邱春岳、曾孫俞沾恩立。”俞賓梅知大真人府贊教,又奉凈明道的祖師,則其身份當為正一道士。
明初太祖朱元璋重正一而抑全真,北方全真多隱匿山林默默修真,然因著多宗派的背景,江南的全真道士依然十分活躍,陳教友亦認為,“當明之世,全真之顯著者多出南方,而北方無聞焉。”
全真道士的社會影響力
在正一貴盛的明代社會,江南的全真道士一方面在內心堅守全真之根基,另一方面又通過兼修正一法術而謀求在社會中的影響力,從而模糊其作為全真道士的身份而取得社會認同,并積極與社會各階層的廣泛接觸,特別是與官僚階層的交往而提升社會地位。
明代的中央乃至地方的道官多為正一道士所掌領,然而江南地區的不少全真道士,亦有能通過其個人的社會影響力而掌領道官職位,如明初全真道士倪玄素位至蘇州府道紀司副都紀、全真道士張守常(張靜庵)職任杭州府道紀司副都紀,明成化間長春庵道士沈繼升職為杭州府道紀司都紀等,都表現了江南全真道士在當時政治社會中的重要影響力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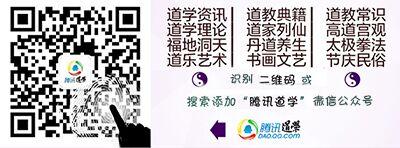
(騰訊道學獨家稿件,作者劉康樂,轉載請注明出處。)
來源中國道家養生網 www.tbbhh.cn
